内容摘要
本文从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议题出发,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就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做出了多重比较。在现代主义之后,后现代主义时期可能是西方历史上最后一个由“主义”引领、参与者广泛的文化创新时期。虽然后现代主义已经式微,其核心议题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艺术成果至今仍具价值,对于面临现代化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尤具启发意义。后现代主义之后虽然不会产生“后-后现代主义”,但不同地域的文化群体,还会在新的现代性境遇下,结合自身的传统,探索和思考超越现代性的可能。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现代性、全球化、历史终结、当代艺术
1 后现代主义在哪些方面不同于现代主义
从构词法来看,现代主义(Modernism)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共同点在作为后缀的“主义”(ism),不同点在作为前缀的“后”(post)。“后”,作为一种历史分期方式,既意味着时间上的“之后”,也意味着“之后”与“之前”大不相同,彼此对立,甚至取而代之。20世纪7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崛起,现代主义一次又一次被宣告死亡。例如,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1939—2019)宣称:1972年7月15日下午3点32分,现代建筑死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1]对于詹克斯来说,现代主义不会一下子就死去,而是会在反复挣扎中走向自我消亡。后来,他在《批判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向何处去?》(2007)中,将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在1968年到1993年之间,标注出现代主义的十个濒死时刻。[2]现代主义在建筑领域的死亡是最易让人察觉的。正是在1980年首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甚嚣尘上的后现代主义使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产生了警觉。这位法兰克福学派最后的传人拍案而起,针对建筑中的新历史主义和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为现代主义未竟的启蒙事业摇旗呐喊。[3]在建筑界,流亡美国的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等人则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便遭到下一代人的挑战,起而为包豪斯精神及现代主义设计理想做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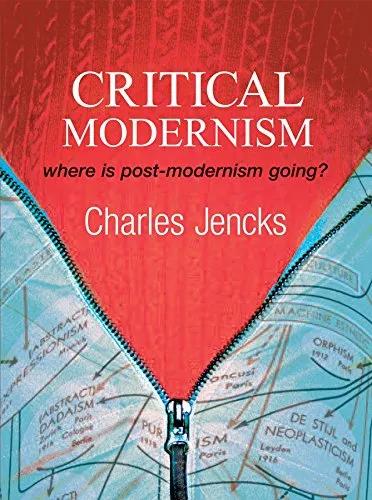
查尔斯·詹克斯,《批判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向何处去》,2007
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主义入手,以现代主义之死换得了自己的新生。不过,按照同样的逻辑,后现代主义也会在批判声中死去。其中广为人知的一次死亡事件,发生在1990年9月16日的《纽约时报》艺术评论栏目。安迪·格伦伯格(Andy Grundberg)教授以《谁都难逃一死,后现代主义也不例外》为题,宣告了后现代主义的死亡。格伦伯格关心的是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在他眼中,后现代艺术崛起的标志是道格拉斯·克林普(Douglas Crimp)在1977年秋天策划的《图片》(Pictures)展。[4]但是,格伦伯格注意到,新一代艺术家不再对后现代主义感兴趣,他们或者转向艺术的精神价值,或者转向更直接的艺术行动,就连克林普自己也不再沉迷于分析“电视、电影和广告”中的大众文化图像,而是针对艾滋病问题采取了更直接的行动。[5]
由于“后”带有强烈的历史断代意味,人们因此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期待:既然在现代主义之后有后现代主义,那么在后现代主义之后,有没有可能出现“后-后现代主义”呢?然而,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然后。在后现代主义式微的20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有关全球化与在地化、历史终结与文化多元主义、当代艺术与当代性、艺术体制与社会介入式艺术的讨论占据了思想界、艺术界的视野。后现代主义艺术似乎整个地消融进当代艺术中,成为1945年至今西方当代艺术史中的一个早期过渡阶段,且在该阶段上,并非所有战后新前卫艺术都可以被纳入后现代主义解释的框架。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借助历史断代建立自身合法性的话语体系,依赖于对现代主义话语及其艺术、设计实践的阐释和批判。不过,后现代主义所描述的现代主义艺术和设计,并不一定符合历史原貌。例如,后现代主义质疑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1909—1994)的现代主义叙事,但格林伯格的现代艺术史本身就有所取舍,不能全面代表复杂而丰富的欧洲现代主义艺术潮流。文丘里(Robert Venturi,1925—2018)、詹克斯对包豪斯及现代主义设计理念的概括和批判,也存在以偏概全、不够客观的地方。不过,关于什么是现代主义,人们一般能够达成共识。与之相比,后现代主义的共同特征更难概括,甚至连哈桑(Ihab Hassan,1925—2015)——较早就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特征进行系统对比的文艺理论家——也承认“后现代主义”一词具有不确定性,人们对它的理解因人而异。的确,人们很容易在艺术博物馆中看到一部完整的现代主义艺术史,却很难看到一部后现代主义艺术史。这或许是因为,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主义”,作为某种引领文艺实践的“意识形态”(ideology),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具有不同的特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具有较高抽象程度的概括词,与立体主义、照相写实主义等具体的艺术运动名称不在同一个理论层面上。“现代主义”更多的是从艺术实践及对艺术家的创作理论中概括而来的,而这些艺术实践或多或少都与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反应有关;而“后现代主义”更多地产生于理论家们对文化艺术现象的解读(后现代建筑是一个例外,介于理论化写作与社会实践之间)。例如,安迪·沃霍尔等波普艺术家在创作时并没有考虑到利奥塔后来概括的后现代状况,也读不懂如经院哲学般晦涩难解的法国后现代理论,却并不妨碍他们的作品成为后现代理论的阐释对象。简言之,现代主义话语更多来自一个“至下而上”的艺术实践领域——19世纪下半叶到“二战”之前以巴黎、维也纳、苏黎世、慕尼黑、柏林等现代都市为中心的欧洲各国艺术家的密切交往和互动——其对应的艺术流派虽然形态各异,却不难找到相互交织的艺术观念、前后相承的艺术发展逻辑。当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1902—1981)1936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划“立体主义和抽象艺术”大展时,他所勾勒的现代主义艺术发展谱系并非空穴来风。与此相对照,后现代主义话语则更多来自学院派知识生产,充斥着来自欧洲的左派批判理论,特别是随1968年学生运动而兴盛的法国哲学。那些被命名为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术语,以“至上而下”的方式传播和渗透到以策展人、批评家为中心的当代艺术世界。从时间范围来看,现代主义比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时间更长,前者有百余年,后者只有近三十年。从空间范围来看,后现代主义在地理传播范围、人文艺术跨界幅度等方面不逊色于现代主义,只不过由于后现代主义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更太平、分工更细致的时代,因此,与野蛮生长的现代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显得更为“体制内”。不过,从创新活力来看,后现代主义并不逊色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是在以欧洲为中心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产生的,在这个风云际会、主义盛行的时代,充满乌托邦渴望、朝向未来的创新创造活力被广泛激发出来。后现代主义诞生于以美国为中心的新资本主义时期,这是一个消费文化盛行的时代,也是一个随战后婴儿潮和1968年学生运动兴起的感性革命时代。后现代主义虽然反乌托邦和进步史观,质疑从无到有的创新和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其本身却以文化前卫自居,富含思想活力和创新冲动。可以说,在现代主义之后,后现代主义时期可能是西方历史上最后一个由“主义”引领、参与者广泛的文化创新时期。后现代主义者对一系列公共问题的讨论,对一系列新术语、新理论的发明和相互引用,横跨了从哲学到文学、影视、建筑、艺术和设计的整个西方思想文化领域,其后又扩散到世界各地。
2 后现代主义核心议题之一:反思和超越现代性
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因其丰富的思想文化创造力而被载入史册。在此意义上,它们的“终结”并不代表“死亡”,而是成为一种活着的思想文化遗产,成为被反复解读的作品和文献。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逐渐消融到当代艺术中,成为当代艺术的一部分。如何在当代艺术中区分出后现代主义?主流当代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观念性和思想性,也即:不是从艺术门类或媒介出发探求艺术自身规律,而是围绕一个又一个带有现实意义的议题展开艺术实践。或许,不是从某种艺术风格或一两个流行术语出发,而是从核心议题出发,是理解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之独特性的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本文认为,后现代主义触及的两个核心议题是:(1)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反思现代性,探索超越现代性的可能性;(2)思考精英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探索打破文化等级制的可行性。正是从这两个迄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核心议题出发,后现代主义在思想史和艺术史上建立起自身的价值。现在先来看第一个议题。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最大不满,是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拥抱或对解决现代性问题的乐观。无疑,并非所有现代主义艺术都具有这种特征,但其中一些的确如此。如歌颂机器的速度和力量的未来主义,俄国构成主义对新技术的崇拜,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一书结尾通过“建筑或革命”这个二元选项所表现出来的乐观情绪……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奥斯维辛、极权主义,历史的实际走向并未支持现代主义的乐观期待。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一书中,将上述这种乐观主义称为宏大叙事或元叙事。在他看来,科技的进步、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不会支持有关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元叙事,反倒会取消其合法性。他说,“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怀疑大概是科学进步的结果,但这种进步也以怀疑为前提”[6]。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
与现代主义的乐观相对照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怀疑。欧洲既是现代化的发源地,也是反现代性的策源地。法国后现代哲学接续了浪漫主义以来的反现代性议题,在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信息社会等新的时代语境下再次激活了这一议题,为形形色色的艺术和社会激进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例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揭示出现代性对身心所具有的更隐蔽、更深层次的塑造作用,有助于帮助人们探寻一条超越现代性的道路——从思想的去蔽,到艺术的解放和日常生活中的革命。不过,福柯之外的大多数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对现代性的“怀疑”和“批判”均缺乏明确的指向。他们将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索绪尔杂糅到一起,沉迷于言意之辨和说不可说的快感,以一种文学化的方式进行哲学写作——不断重复一些晦涩难懂的术语,如块茎、阉割、凝视、延异、游牧、无器官身体等,不是用它们去论理,而是将这些概念当作“心灵图画”(如德勒兹用“块茎”而不是“树”来隐喻知识生产),到自己和读者的心灵内省中寻找感觉的确证——结果给大多数读者带来一种莫测高深、似懂非懂的阅读感受。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等之前的哲学流派相比,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法国后现代哲学,丧失了对真理、本质和普遍性的确信,以相对主义的方式反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他们乐此不疲地揭示真实的不确定性(鲍德里亚、利奥塔)、自我的不确定性(拉康)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德里达、德勒兹)。他们学识渊博、引经据典,却又刻意偏离学术规范,将自己打扮成带有前卫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热衷于在公共场合或电视上露面,在使哲学大众化的同时却又拒绝使用清楚明白的语言。然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他们掉进了一些最基本的思想陷阱而不自知。这些陷阱,多数都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笔记中被反复提到过,但是大多数人,特别是哲学爱好者和初级反省者都难以规避。利奥塔似乎读过维特根斯坦,但他对“语言游戏”的相对主义理解与维特根斯坦的原意相去甚远。德里达的哲学大厦建立在对词与物、意义与指称关系的思考上,但他似乎不了解维特根斯坦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巴特勒(Christopher Butler)撰写了一本看似通俗易懂的《后现代主义简论》(Postmoder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2002),被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当作“通识读本”引入中国。然而,这本书并不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普及介绍,而是从英美分析哲学出发,逐条对法国后现代哲学提出批评。例如,他在书中提道,“在德里达试图批驳索绪尔的理论时(见《论书写》),他显然并不知道,在哲学界(包括法国哲学界)看来,许多他所关心的问题以及他自己得出的(让人难以把握的)结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早就谈到过,而且表述得更加清楚,研究得更为缜密。当然,这种无知对德里达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德里达在早期作品中并未提及维特根斯坦。许多研究德里达的文论家们也因此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历史一无所知,不知道英美哲学传统对这些哲学问题早就提出过一些规范性的解答”[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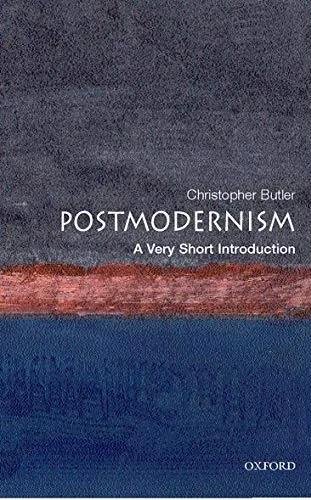
托弗·巴特勒,《后现代主义简论》,2002
文学化写作极大地削弱了法国后现代哲学家讨论现代性问题的力度,但他们最隐秘的愿望,却是在启蒙和乌托邦谋划失败后去追寻超越现代性、反抗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使得他们的写作与现实产生了曲折的联系。此外,他们的写作虽然学究气十足,却因其反主流、反中心、反常规的态度,广泛启发和影响了前卫艺术家的创作,以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带有解放意义的社会文化运动。相对主义常常能够为边缘人和反叛者提供思想武器,这或许是后现代主义对艺术和社会激进运动产生吸引力的一个原因。与法国后现代哲学的含糊晦涩相比,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1955—)及《十月》群体的后现代文艺批评理论,尤其是北美的后现代建筑理论,对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讨论要清晰明了得多,也更富于建设性和现实意义。简·雅各布森(Jane Jacobs,1916—2006)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1925—2018)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1966)、《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建筑形式领域中被遗忘的象征主义》(1972),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1939—2019)的《后现代建筑的语言》(1977)、《现代主义的临界点——后现代主义向何处去?》(2007)等著作已成为建筑理论经典,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与柯布西耶的建筑和城市规划不同,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为解决都市病提供了一套接近自由主义的方案:传统与现代的并存,城市的自然生长, 空间的多元功能,建筑的多重编码,交通和信息导引的人性化。城市规划、建筑、环境和空间设计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最为深广,改变其主导性的思想观念,对于现实的改进至关重要。如果说粗放型现代化使得千城一面、传统中断、乡村衰落、世界去魅、生活乏味,后现代建筑理论则为城市化转型指出了方向。这种理论,对于现代化、城市化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尤具借鉴意义。
3 后现代主义核心议题之二:精英艺术与大众文化
后现代主义引人注目的另一个议题是如何颠覆“高与低”“中心与边缘”的文化等级秩序,打破精英艺术与大众文化、艺术媒介与大众传媒的边界。最典型的案例是产生于英美的波普艺术(这或许让法国哲学有些尴尬)。文丘里、詹克斯常常将后现代建筑与波普艺术相提并论,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潜在的原因,是他们关心艺术的内容胜过关心艺术的形式。功能决定形式,但是在功能和形式之外,受众还需要内容和信息——历史的、情感的或实用的信息。在此意义上,反功能主义的后现代建筑在波普艺术创作中找到了共鸣。结构主义将作品(work)理解为文本(text),作品的意义不是自足的,而是依赖于创作者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上下文(context)。后结构主义接续了这一思想,将任何一个文本或表征(representation)都理解为一个无穷无尽的编码(encode)和解码(decode)过程。在此意义上,我们不是去“看”(seeing)作品,而是去“读”(reading)作品。这与形式主义对艺术的理解大相径庭。传统和古典艺术充斥着大量的题材和形象,“看不看得懂”是品评作品的一条潜规则,这里的“看”也即“读”。现代主义盛期的抽象艺术,通过摒弃题材、凸显形式而拒绝被阅读,对于这样的作品,“看不看得懂”是一种外行的品评标准。在这一时期,立体主义虽然将报纸和文字拼贴进画面,使作品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但其重心并不在内容而在于形式;柏林达达主义的照片蒙太奇,将社会政治内容拼贴进作品,通俗易懂,一目了然,但就艺术创作本身而言并不成功;受到弗洛伊德主义影响的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在一战后的巴黎的重聚),使具象描绘成为创作的重心,但除画家本人所领悟的心理意义外,观众并不真能从画面上解读出带有公共性的意义来。一战时期从巴黎来到纽约、二战后在美国成名的法国艺术家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将源于欧洲的现成图像、现成物品创作方法带到美国,并通过他那件“臭名昭著”的小便池使其家喻户晓。杜尚在巴黎时即已开始从事现成品创作,但到了纽约后才将这种独立而非拼装式的“拾得物”(found object)命名为“现成品”(readymade)。拼贴或拼装,仍然是将寻常物置入作品的整体构造之中,与抽象艺术的形式构造原则相去不远。杜尚的现成品创作却与此不同。杜尚关注非艺术的内容更胜于艺术技法本身。他借现成品创造出不是艺术作品的作品,颠覆了传统美学对艺术作品的设定,为艺术创作开辟了新的方向。杜尚在艺术史上获得成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除了自身的艺术才能和思想特质,也得益于外在的历史形势。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外部原因:一是世界艺术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巴黎转移到纽约,而杜尚恰好离开巴黎来到了纽约;二是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崛起的波普艺术、概念艺术等享誉世界的艺术流派对杜尚的追随和认可。

杜尚和他的作品
1964年,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1925—2008)在为威尼斯双年展美国馆撰写目录时提到,“每个人都知道世界艺术的中心不再是巴黎,而是纽约”[8]。这一年,杜尚的大型回顾展在五家美国博物馆巡回展出。也正是在这一年,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在纽约马厩画廊举办了他的第一个雕塑个展,丝网印仿制的布里洛包装盒层层叠叠堆放在展厅,进入其中的观众犹如进入了超市。超级市场这种批量化、标准化的零售模式,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在20世纪50、60年代进入高速增长时期,构成了波普一代人的成长和生活环境。

安迪·沃霍尔和他的布里洛盒子
安迪·沃霍尔对杜尚推崇备至,专门为杜尚拍摄过一部长达20分钟的肖像短片。杜尚对安迪·沃霍尔也赞赏有加,在接受报社记者采访时曾多次提及沃霍尔,“您拿一盒金宝罐头汤,然后重复画上50遍,您对视网膜画像也就不再感兴趣了。您所感兴趣的,正是促使您将50盒金宝罐头汤放在同一画布上的设想”[9]。不过,杜尚只是按照自己的设想去解读沃霍尔的《金宝汤罐》,他所关心的是如何摆脱架上绘画和审美观念的历史纠缠,这一议题启发了概念艺术运动和“去物质化”的策展理念,却不是波普艺术关注的焦点。

杰夫·昆斯和他的作品
看过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展,阿瑟·丹托(Arthur Danto,1924—2013)写出了《艺术世界》(1964)这篇具有决定意义的论文。丹托接受了现成品的挑战,革新了美学对艺术的定义。不过,丹托同样没有完全理解沃霍尔等新一代艺术家的使命(虽然年龄接近,但他认为自己在艺术上属于抽象表现主义一代),他实际上是回到杜尚的现成品概念,从杜尚的视角来看待波普艺术。然而,在杜尚将一件商品无差别地挑选出来、使其成为一件现成品的地方,沃霍尔这代人从中看到的却不仅仅是一件单纯的人工制品,而是塑造大众生活的商品。在沃霍尔之后,杰夫·昆斯(Jeff Koons,1955—)以展示商品的形式展现成为艺术品的寻常物(commonplace),进一步凸显了环绕在商品周围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或“灵韵”(au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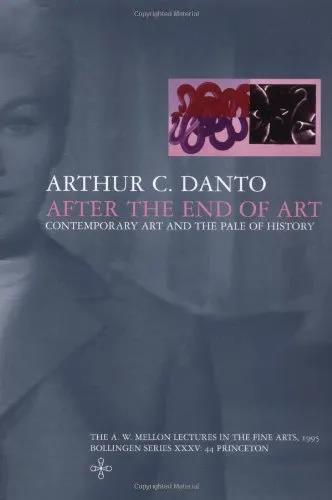
阿瑟·丹托,《艺术终结之后》,1998
艺术的一半是非艺术,这部分内容主要体现为作品的题材和主题。与抽象艺术相比,波普艺术不仅使题材、主题等艺术之外的社会内容回归艺术,而且从杜尚的现成品创作模式出发,革新了作品与题材的关系。在现实主义创作中,艺术家需要到生活中收集素材,将素材加工提炼为作品的题材和主题,赋予它们以形象和形式。而在波普艺术中,已经被社会加工好了的题材和形象——无论是精美的包装、发光的橱窗或诱人的商品广告,还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对象的电影明星——直接被挪用到艺术作品中,与艺术世界的上下文产生共振。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与当代艺术的关联,以及围绕着这一关联展开的后现代议题,就在这种共振中产生了。由此产生的挪用、反讽、戏仿、混搭等创作方式,被命名为典型的后现代艺术手法。后现代主义借此找到了一条超越现代性的途径:不是去颠覆资本主义,也不是去寻找乌托邦,而是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保持清醒,在生活和社会表征(representation)中解码和阅读现代性精神分裂症的梦呓。德波(Guy Debord,1931—1994)将被资本操控的表征称为“景观”(spectacle),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则将它称为“拟像”(simulacrum)或“超级真实”(hyperreality)。在他们看来,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为人们所在的世界编织了一张等大的地图,覆盖了全部的生活领域;人们所见的一切都是被虚拟出来的,无从摆脱也不可能摆脱,因为景观背后已无真相。从德波发起参与的情境国际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随社会介入式艺术而兴起的关系美学,以更为直接的行动替代了后现代主义面对现代性困境的犹疑态度。从根本上来说,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是无法被超越的,在此意义上,利奥塔将“后现代”(post-modern)解读为“再现代”(re-modern),理解为现代性不断否定自己又不断重启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主义触及了如何超越现代性这个议题,却并未提供一条出路;触及了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这一现代性的新议题,揭示了资本对世界无所不在的操控,却并未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后现代主义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也未尝不可将后现代主义称之为某种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惨绝人寰的奥斯维辛,人类得到了一个深刻教训:宁可要现实主义的悲观,也不要理想主义的乐观。后现代主义正是某种带有悲观情调、时刻持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被后现代主义赏识的波普艺术,也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只不过,与喋喋不休的后现代哲学相比,波普艺术的表述方式要干净利落得多。崛起于欧洲的新表现主义绘画,常常被看作是波普艺术、后现代艺术的挑战者和替代者。但是,无论是在现实性还是在前卫性上,新表现主义绘画都无法与波普艺术相比拟。新表现主义不仅因迷信内在体验的独创性而在思想上落伍,也无视现实的视觉文化环境,使艺术创作隔绝于当代。从沃霍尔、杰夫·昆斯到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1962—)、布莱恩·唐纳利(Brian Donnelly,1974—)的艺术生产,其最大特色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艺术商业化,而是将商业力量征用为艺术的能量,通过大众传播渠道和流行形象重新建立起作品与现实世界、艺术家与观众的关联。这样的艺术,无疑是更具当代精神的艺术。
4 后现代主义之后是什么
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式微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两个世界融合为一个世界,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一个热门议题。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不仅是指商品跨越国界产生世界贸易,而是指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全球趋同,由此产生跨国公司、跨国阶层、跨国文化等新现象。艺术双年展、艺术节、设计周在全球,特别是在非西方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艺术家跨国工作室、明星建筑师和地标建筑、创意产业和创意城市的全球竞争……人们在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相同或相似的艺术面孔。荷兰艺术家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1977—)的《大黄鸭》(2007)再一次革新了现成品的利用方式,赋予充气玩具以不同于杰夫·昆斯的意义——以全球化为主题,并将全球化产生的能量置入作品内部,使廉价的充气玩具鸭成为移动的地标建筑,点亮全球化时代一个又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大黄鸭这个不带民族、地域特色的超扁平形象,成为全球化时代最好的象征和沟通媒介。

霍夫曼,《大黄鸭》,中国香港,2013
1992年,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曾乐观地预言,后89时代是一个历史终结的时代。后现代主义曾试图通过对宏大叙事和元叙事的批判而终结历史,现在历史真的“终结”了。就此而言,也就不再可能出现“后-后现代主义”等基于线性历史的叙事方式了。然而,2001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人们忽然意识到世界并不统一,民族、国家和文化冲突并未停止,历史并未“终结”。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泛滥、中美之间愈演愈烈的贸易战,更是加剧了全球经济体的分裂。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国际,获得了西方艺术世界的认可。回顾这段历史,一些人会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对西方人的猎奇和中国艺术家的崇洋媚外进行反省和批判。然而,20世纪90年代,也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开端。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西方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崛起并成为世界新的一极为世人所公认。在此意义上,中国当代艺术并未因融入西方而终结,而是恰好在此时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在当今的艺术世界,与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相反的趋势是艺术的在地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复苏。以中国为例,在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从西方横向移植的艺术和艺术观念,对于本土传统构成了一个又一个挑战,再加上此起彼伏的战乱和政治运动,使得中国的艺术传统没有机会像欧洲和日本艺术传统那样自然地融入现代化进程,而是不断被污名化,屡屡遭到人为的破坏。中国经济全面复兴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也就摆上了当代艺术的议事日程。是继续走“中西融合”“西体中用”等以西方艺术为参照的现代化道路,还是给予以活态形式留存至今的传统艺术形式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回到现代化的开端,再一次完成传统艺术的现代和当代转化?在西方人认为艺术史终结的地方,中国的当代艺术史或许刚刚开始。全球化带来的共同繁荣,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崛起,颠覆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模式。后殖民主义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主张以空间的多元取代时间的一元。然而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而言,线性的历史被横向的、全球均质的空间所取代,恰好意味着民族传统的中断。村上隆曾用“超扁平”“幼稚”来命名历史被阉割后的日本当代生存状态,用“卡哇伊”的欢乐表情表达一种无声的悲哀。很多人惑于“二次元”等表面现象,对村上隆的深刻思想缺乏认知。村上隆与不少中国艺术家一样,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民族的前途命运十分关心。当传统文化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得以复兴之际,扁平的空间又会被重新还原为延绵的时间,获得生长和积累的可能。在现代化、西化过程中一度被打断的中国艺术史,在新的时代机遇下,获得了重新接续和生长的可能。这种重新接续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现代化为前提进行的一种自我修补、自我更新。以此为基础的创新,是有主心骨的创新,而不是附庸性的追随、模仿和复制。唯有这种创新,才有可能对世界文化产生真正的贡献。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古往今来并不存在以单一轴线书写的历史。全球化意味着多条历史线索的交织。中国的崛起并不会改变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格局,反过来还会促进这种“和而不同”的天下大同。现代化带来的违背人性的负面结果,是所有人都必须面对,也是需要采取智慧的方式加以解决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往往只接受西方拥抱现代性的一面,却忽视西方反现代性的一面,这是由某种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在今日之中国,如何超越现代性、建构一种融通古今的当代文化,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由此产生的结果,不会是重走后现代主义的老路,而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一度时髦和流行,如今已归于沉寂。新的思想将在新的社会需求和新的愿望产生之际萌芽,其前提条件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自己的现代性。当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叙事终结之时,后现代主义从逻辑上已无“后-后现代主义”之可能。然而,后现代主义留下的思想遗产,如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对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尊重、对情感和多元化需求的关切、对自然生长而不是揠苗助长的推崇,这些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特别是对于正处在新的转型时期的中国是有启迪意义的。

《爱德蒙·贝拉米肖像》,2018
后现代主义之后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是“后-后现代主义”,也不会是对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某种简单重复。人类走进了现代化的深处,在地球不同区域生活的人群,都有必要再次反思现代性,对现代化的走向进行审慎的选择。近十年来,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已开始威胁和挑战人类的存在。2018年10月,佳士得纽约拍卖行拍卖了一幅由人工智能创作的绘画作品《爱德蒙·贝拉米肖像》。肖像暧昧不清,像极了人工智能开启自身历史后对已消亡的人类先祖的模糊记忆。生存还是毁灭,古老的问题重新回响在人类耳畔。只有人类才能爱人类,只有人类才能拯救人类自己。21世纪最重要的文化议题,或许仍然是如何协调人的情感需求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注释:
[1] Jencks, Charles. 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M].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Inc, 1977:9.[2] [美] 查尔斯·詹克斯:《现代主义的临界点——后现代主义向何处去?》[M],丁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8页。[3] Habermas, Jürgen.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J].New German Critique, No. 22, Special Issue on Modernism, Winter 1981: 3.[4] Crimp, Douglas. Pictures[J]. October, 1979.8: 75-88.[5] Grundberg, Andy. As It Must to All, Death Comes to Post-Modernism[N]. The New York Times, 1990-9-16.[6] [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4页。[7] [英] 巴特勒:《解读后现代主义》[M],朱刚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第152—153页。[8] [法] 伍泽:《杜尚传》[M],袁俊生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第506页。[9]同上,第499页。
作者:陈岸瑛,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
发表在:《装饰》2021年第3期